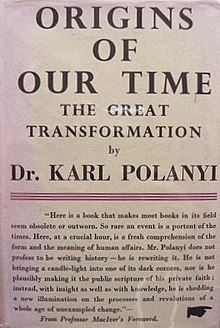布達佩斯的故事
:
(日)栗本慎一郎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品方:
三輝圖書副標題:探索現代思想的源流
原作名:ブダペスト物語現代思想の源流をたずねて譯者 :
孫傳釗出版年: 2012-6頁數: 242定價: 35.00元裝幀:平裝 ISBN: 9787542637673
內容簡介 · · · · · ·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與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一位是公認的20世紀最徹底、最有辨識力的經濟史學家、社會思想家,一位被評價為歐洲最卓越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彼得·德魯克在《旁觀者》中對他們的記敘令讀者震驚於其家族的天賦與影響力,卻也令人遺憾地錯誤百出。
1980年代初,栗本慎一郎親身前往匈牙利考察,並與分佈在全世界的幾乎所有波蘭尼家族成員取得聯繫,完成這本“執拗地追究根源”的思想隨筆。可以從中一窺波蘭尼兄弟學術理念的源頭,也可了解到波蘭尼家族及周圍文化人的活動對匈牙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產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引發了1918年匈牙利革命,也一直延續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甚至冷戰結束後的今天。
波蘭尼一家是20世紀初讓布達佩斯沸騰起來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家族,也是了解這段布達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線索和鑰匙。
也許是一種過分偶然的巧合,這些天才的大師都屬於同一世代、處在同一城市,而且不僅學術,就連藝術的精神取向在深處也是相通的。
——栗本慎一郎
作者簡介 · · · · · ·
作者介紹:
[日]栗本慎一郎日本著名的經濟人類學家、法律社會學家、評論家。1941年生於日本東京。1971年在慶應義塾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1976年成為明治大學教授,1991年為“明治大學招生腐敗案”憤然辭去教授職位,走上從政道路。曾任國會眾議員、經濟企劃廳政務次長。1999年因患腦梗塞淡出政界。先後擔任拓殖大學客座教授、帝京大學客座教授、東京農業大學教授。2011年出任日本有明教育藝術短期大學校長。著有人類學三部曲《穿褲子的猴子》、《扔掉褲子的猴子》、《脫掉褲子的猴子》及《經濟人類學》等影響廣泛的著作。
譯者:
孫傳釗1949年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1990年代遊學於海外。現專注於翻譯和撰寫書評,譯有《民主極權主義的起源》、《韋伯論大學》等學術著作,書評多刊於《二十一世紀》、《讀書》、《中國圖書評論》等。
目錄 · · · · · ·
目錄
第一章多瑙河畔血色的薔薇花
第二章迎接革命與恐怖暴風雨的來臨——波蘭尼的一家
第三章暴風雨中翱翔的孔雀——布達佩斯精神史的序幕
第四章為誰劃破夜空的流星
第五章燃燒的布達佩斯
第六章布達佩斯的藝術家們——盛行的革命大眾文化
第七章布達佩斯送來的禮物——邁克爾·波蘭尼的“深層的知”理論
後記
· · · · · · ( 收起 )
"布達佩斯的故事"試讀 · · · · · ·
我們追求自由和正義的鬥爭閃耀著榮光。匈牙利革命啊,永遠在我們前面閃射出耀眼的 光芒!——科茲托尼·佩特爾《基里安兵營日記》 一觸摸你,我們的指端就會湧出血來。你就是朦朧的、貧困的匈牙利!你還活著?我們還保持著活力?——阿迪·安德烈《匈牙利雅各賓黨黨歌》 布達佩斯的彈痕1980年9月11日下午兩點,我佇立在美麗的斜拉索橋...
第一章多瑙河畔血色的薔薇花第二章迎接革命與恐怖暴風雨的來臨——波蘭尼的一家《布達佩斯的故事》試讀:第一章多瑙河畔血色的薔薇花
我們追求自由和正義的鬥爭閃耀著榮光。匈牙利革命啊,永遠在我們前面閃射出耀眼的 光芒!——科茲托尼·佩特爾《基里安兵營日記》 一觸摸你,我們的指端就會湧出血來。你就是朦朧的、貧困的匈牙利!你還活著?我們還保持著活力?——阿迪·安德烈《匈牙利雅各賓黨黨歌》 布達佩斯的彈痕1980年9月11日下午兩點,我佇立在美麗的斜拉索橋(Széchenyi Lanchid)邊上,身後是國立科學院的大門,面對著羅塞凡爾特(Roosevelt)廣場——一個中等規模的廣場。也是在這個廣場對面,矗立著一幢叫做“葛蘭夏姆廣場(Gresham Palace)“的大樓,是舊時英國葛蘭夏姆保險公司建造的。這是一幢上充滿巴洛克風格,又帶有世紀交替時代新藝術(Art Nouveau)運動具有的那種過度裝飾的特點的建築物。這幢建築物正面對著斜拉索橋的出口,大門邊的石壁上,依然殘留著尚未修復的彈痕。若仔細看一下,您會發現這些彈痕猶如歲月流逝中的自然缺損,卻又能分辨出比較陳舊和歷史相對短暫不同的兩種彈痕。陳舊的彈痕出自1918年革命,而比較新的彈痕是1956年革命時巷戰留下的紀念。大約在一個月前,探究這部分精緻的金屬工藝品明顯受到現代藝術影響的原因、特別是探究匈牙利風格的建築物及其與至今沒有修復的彈痕形成對比之原因,對我來說有很大的魅力。我為此拿著照相機在這一建築物前轉來轉去時,兩位匈牙利出身的加拿大人與我攀談起來。更早一些時候,拿著照相機擠入觀光人群的我,已經註意到這兩位面善的老人——他們盡量避免擠到他人,還堅持留在這擁擠的人流中,顯然他們對身邊的人們感興趣。從入口進去5米左右,有一扇配有精緻的用金屬雕塑成匈牙利國鳥孔雀的大門,為了看到樓裡暗處精湛的細節,我拿著照相機——猶如拿著一把槍正想“衝進去”當口,那位50歲左右的老紳士問我:“我也感到這座建築很有趣,您為何也對它很感興趣?” “那是因為它的風格和式樣與那牆上的彈痕形成一種對比。”我答道。可能他對我的舉動比對這座建築更感興趣,聽我說到彈痕,他想說什麼,卻欲言又止,把話題扯開,說些別的,然後與我一起登上了觀光巴士。他告訴我,曾好幾次來到父母的祖國匈牙利。但是這次夫妻倆坐觀光巴士旅行能去各個名勝之處,一定比先前自己一個人到處亂轉更開心。他們夫妻倆這次是由他的母親——一個完全具有典型的馬扎爾人長相的母親帶領來到匈牙利的。“匈牙利人還應該多保護一些建築物,可是……”,他一邊說一邊眼睛轉向牆上的彈痕,其實,他想說的那些事情,也是我以後關心的事情。喜歡布達佩斯的外國人都讚不絕口:“漂亮!好漂亮的城市!”實際上這個城市的建築看上去很陳舊,牆上塗料都脫落得斑斑駁駁駁。但是,當然因為馬路很乾淨,所以給人的印像說得上整潔、漂亮。一走進大街背後的小巷,還能見到支撐著那些似乎搖搖欲墜一個世紀前的老房子及住在裡面的居民。這不僅顯示了這些老房子沒有來得及修繕,也表明了新的建設的姍姍來遲。其實,布達佩斯人也很在意這種情形,人們一問起這事情,他們就顯出一種自尊心受到傷害的表情。他們很清楚布達佩斯建築物的價值,在導遊時會做詳細的解說,甚至還相當詳細介紹美術著作中涉及建築的內容。說實話,布達佩斯建築之所以沒能修繕一新顯示出的蒼老和疲憊,是因為經濟拮据的原因。當然在城市的各處馬路上,也能看到一些腳手架——正在大修,但是從整體來看,只能說終究還是絕少數。無論是1918年的“菊花革命”留下的彈痕,還是1956年事件留下的彈痕,都還沒有完全填補、塗刷一新,猶如紀念物“保留”在那裡,有的彈殼還鑲嵌在牆上的水泥裡,很多建築物斑駁是“保留”在那裡的彈痕,而不是建築物上的自然剝落的斑痕。如果用水泥來填補的話,可以馬上消除這些彈痕,沒有消除這些彈痕,其實是人們故意不去填補,所以,“保留”這些彈痕也是一種人為的“選擇”。也許這位來自加拿大的朋友也想說這樣的話。攀談中我與這對加拿大夫婦及其母親很快相互熟悉起來,一起上了觀光巴士。巴士上的導遊是一位中年婦女,是一位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少見的熱心工作的女性,不斷熟練地交替用英語和德語進行解說,有時最終還把英語和德語混雜起來解說,讓遊客反而感到困惑而苦笑。當巴士經過多瑙河上那座美麗的斜拉索橋,駛近建立在布達的高地上的王宮時,我犯了一個低級錯誤——看到王宮的外牆,我小聲叫了起來:“多厲害的彈痕!”——其實那是一片特意用凹凸不平石片裝飾的牆面。在一個月前,9月11日那時候,我的眼睛還沒有熟悉布達佩斯這座城市,也沒有看慣這裡的彈痕。雖然城裡留下了無數的彈痕,當然,很多時候,人們稍不在意,不會注意到這些彈痕,或者會把它們誤為自然剝落。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誤會,除了我前面已經提到的,即自然剝落那部分,顏色也自然風化,所以彈痕與其他部分相比並不分明;此外另一個原因是具有各種屈辱感的布達佩斯市民都不會輕易明確告訴我,或用表情向我暗示:“這是1956年市民們與蘇軍巷戰交火留下的彈痕。” 屈辱的布達佩斯市民實際上現在還有30萬左右蘇軍駐紮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去世時,曾有相當緊張的戰備行動,使得不少關心國際局勢的人們緊張起來,因為蘇軍的坦克向著匈南邊境開去。這個蘇聯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匈牙利的“朋友”。1956年10月爆發的匈牙利革命,因為民眾與這個“朋友”展開了巷戰,所以現在對下一代的孩子們的教育中,都把這場革命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即使開放巷戰戰場,誘導外國遊客參觀;或者相反,即使完全把那些彈痕完全填補塗抹掉,也難以抹去布達佩斯市民那種屈辱的感情。可是,在匈牙利國內幾乎完全看不到蘇軍的士兵,有人說有30萬,也有人說有50萬駐匈蘇軍。他們大致駐紮在發電廠那樣的“據點”裡。因為蘇聯人的無孔不入的干涉、不信任的態度,匈牙利人都直率地說,依然對他們沒有好感。相反,在布達佩斯每個街道都會不期而遇黑市收購美元的男子,如果把收購美元的黑市看作“社會主義”匈牙利的恥辱或創傷,那不過是一種缺乏深究、過分簡單的看法。最近在某個報紙上看到有個記者寫的在整個布達佩斯市內不太能看到熱愛匈牙利的市民的報導。這樣的報導一點也沒有可信之處,完全是謊言。這是無意識地參照某種標準——即匈牙利是個“清廉的、美麗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評價的匈牙利國民的,即使參照這種標準來評價的話,那就犯了錯誤,是雙重的、甚至三重的錯上加錯。因為記者註意的是無數的活躍在街頭的黑市買賣,但是,這完全不是問題(愛國與否的問題——譯者)的本質,問題的本質在其它地方。先前我誤把特意用凹凸不平石片裝飾的牆面看作彈痕小聲叫了起來,讓離開匈牙利流亡加拿大的旅遊者們感到失望而皺眉。然而,也是因為我說了這句說錯了的“俏皮話”,引發了我與他們稍微深入談論了一些與革命事件相關的歷史過程、民族問題等話題,這些話題一下子就使得巴士上那位導遊老阿姨的表面的介紹顯得膚淺乏味,讓人有點掃興。在這樣談話的流程中,完全不允許把這些問題作為“俏皮話”的談資,當時我並不是作為“俏皮話”說出來的。我是把歐洲建築上司空見慣的用石頭裝飾成自然風化的凹凸誤看作是彈痕而不由自主發出了感嘆,雖然那凹凸也做得稍微精細了一點,但不至於被誤認為彈痕。所以“俏皮話”就變得讓人感到是我故意“製作”出來的惡作劇的“俏皮話”,效果很不好。打個比方,就如看到路途有一隻貓伸開四肢朝天躺著,指著這隻貓對人說“你家的老爺子戰死時也是這個模樣。”聽者必然惱火,還要發出苦笑。豈止苦笑,也可以說難過得要死的“死笑”。笑,實際是人活著拼命表達自己的存在一種掩飾外表的演技。人並不都是因為快樂才笑的,也有笑呀、笑呀,笑到最後流出眼淚,有時也是不由自主地爆發出來的瘋狂——狂笑。當然,我的“俏皮話”的後果並沒有那麼嚴重,可也是大失態、犯了大過錯。趕緊尋找出錯的理由,一慌張,我的英語結結巴巴起來。那位加拿大人原先默契地與我約定一起吃晚飯的,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沒有踐約。為何會有這個結果,我想,可能是我自我解嘲多說了一句:“我生來擅長黑色幽默。”這句話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讓人對我敬而遠之。“黑色幽默”確實也是我的品性“特徵”之一。當年搞學生運動舉行示威遊行,被防暴警察包圍得嚴嚴實實時,處於難以保證身體毫髮無損回家的危機之中,我還是要脫口而出說我的“黑色幽默”的俏皮話:“保護好自己的臉和'小弟弟',否則不能結婚了。” 當然,人們都原諒了我。9月11日一整天我犯了不少類似的錯誤。那是個陰天,後來還下起了小雨。可是我依然和布達佩斯朋友一起去瞻仰匈牙利革命紀念碑。布達佩斯的多瑙河 斜拉索橋下奔流的是多瑙河,同樣的多瑙河,這裡與其流 過維也納的上游相比,遠為寬廣。因為布達佩斯的多瑙河處在離開維也納200公里的下游。1872年,布達和佩斯這兩個的城市才合併成一個城市。之前,多瑙河的右岸是布達,左岸是佩斯。那時的布達市被稱為“舊佈達市”。它包含了多瑙河右岸偏於上游的那部分。之所以叫“舊佈達”,因為公元前羅馬人在那裡建築了城堡,比現在的布達市中心遠為歷史悠久。1872年只是簽署了合併條約,布達和佩斯真正合二為一的管理是從1873年開始。從下游數起共有6座橋跨越在橫貫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多瑙河上——貝多芬橋、自由橋、伊麗莎白橋、斜拉索橋、馬爾基特橋和阿爾帕特橋。其中斜拉索橋尤為重要,把佩斯市中心與布達的高地上王宮的入口聯結起來。從下游望去,構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斜拉索橋鑲嵌在中間,左邊是可以俯瞰多瑙河的王宮、漁夫的堡壘,右側是國家科學院;再稍微上游一點,有以高矗起裝飾精細的塔和柱子而顯目的、新復古主義風格的(New Gothic,19世紀歐洲興起的對洛可可、古典主義風格反動的、緬懷中世紀建築風格的新建築藝術樣式。——譯者)的國會大廈。那漁夫的堡壘是古代多瑙河的漁夫為了憑藉自己的好水性來防禦外敵入侵建築的。堡壘的後面是看起來比遠比維也納聖斯替芬教堂地基更加紮實穩固、馬賽克裝飾的屋頂的聖馬蒂烏斯教堂。也是這個原因,昔日維也納的教堂也吸收了馬扎爾文化的要素,都鑲有馬賽克裝飾,匈牙利的城市裡的建築物普遍採用馬賽克裝飾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藝術傾向,在比斜拉索橋更處於上游的馬爾基特橋和與橋相連的療養地馬爾基特島都能看到。更往上游望去,可以看到布達一側王宮邊那個小丘解放廣場上矗立的女神鵰像;佩斯一側則有洲際酒店那樣現代賓館等近代高層建築、布達佩斯大學理學院和貝多芬廣場。從這裡還生活著眾多漁夫、河中馬爾基特島的寬大、左右兩岸各有一個都市等要素可以判斷布達佩斯的多瑙河之寬廣。河流的美麗、斜拉索橋的宏觀、新復古主義風格或巴洛克風格的國會大廈和宮殿,種種景觀點綴,布達佩斯自古以來被稱為“多瑙河畔薔薇花”。多瑙,用馬扎爾語來說,應讀作“多納”,它把布達佩斯分割成兩大半,奔騰不息。“美麗的藍色的多瑙河”的讚詞雖是因維也納而聞名於世,但是布達佩斯的多瑙河的藍色之美及其喧囂遠遠維也納那一段,這裡的人們在多瑙河的橋上、河面上為了生存而不得不作誓死的搏鬥。獻血染紅的多瑙河畔薔薇花 9月11日我身邊終於又聚集了兩、三位匈牙利的朋友,都是通過波拉尼·卡洛伊(卡爾·波蘭尼)認識的。雖然歷史決不會倒轉,但是他們將和我一起追溯1956年革命的踪跡。眾所周知,沒有比1956年布達佩斯市民的英勇的壯舉給整個西歐的左翼更大衝擊的事件了。布達佩斯的市民、工人的口號及其精神中,明顯有從馬扎爾地域傳統文化土壤中汲取營養的志向。即使是從馬扎爾、猶太思想及其文化背景,即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布達佩斯的革命浪潮來考察,“民族”和“地域”都是重要的問題要素。當時西歐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相對反權威主義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群體,與蘇聯共產黨相 比,更加具有現代誌向,其中最典型的是一種變種的存在主義。他們雖然也為蘇聯的“坦克”、“屠殺”對自己的信念產生了動搖,但是,他們的精神誌向並不習慣於馬扎爾人、馬扎爾式的思考,所以,他們並不能把匈牙利革命看作是自己追求的東西,雖說也開始轉入批判斯大林主義,但是他們自己還是有陷入斯大林主義的危險。關於如何對斯大林主義下定義的原則,我想,波蘭尼·米哈伊(邁克爾·波蘭尼)的定義是唯一最有效的了。可以參照他的《默知的維度》(邁克爾·波蘭尼,日文版,由紀伊國書店出版)和拙文《邁克爾·波蘭尼》(《現代思想》1980年12月號,也就是本書最後一章《布達佩斯的禮物》) 波蘭尼·米哈伊已經明確揭示了:可能的心理基礎問題上,存在主義在考慮關於結構改革對,其虛構的外在的道德的追求,超過對實體的結構改革的追求,恐怕這一點在結構主義潮流中發揮很大的作用,雖然有點讓人感到意外。我想,主要是因為西歐知識分子的主流派,與民族文化、思想相比,他們不恰當地輕視民俗問題,所以不能正確對待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比如,薩特最終也沒有能夠理解民族、民俗等能煽起人們激情的根源,不能認識到這個要因,當然不能正確評價匈牙利革命。我這裡要指出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即1960年代日本的安保學生運動倒是受到1956年布達佩斯革命相當深刻的影響。可是我不想在本書中論述其對日本安保運動及其思想的影響,而且這裡也沒有討論的餘地。說起來,原來的目的是為了調查波蘭尼兄弟事蹟的我,對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屬於左翼的波蘭尼兄弟曾涉足的1918年革命及有關1956年革命的事蹟和地名,我要比其他歐洲的旅行者更為了解。因此,雖然我也只不過是日本知識分子中一個小角色,可是,與保守、反動的政治立場無關,我對民族和民俗問題充滿了興趣、我堅持認為儘管被激勵起來的1956年革命浪潮雖然持續了不到一個月,但這是一個廣義上值得探討的科學的課題,這也讓我有勇氣試圖為一、兩位學者充當(該課題的)嚮導。但是,我一開口,馬上又出錯了。這次出錯讓我同感要怎麼也必須有一種設身處地 的感情,否則很容易犯從沉浸在抽象的宇宙論那種形而上學方法的旁觀者來思考的錯誤。這種意義上,也讓我在這次佈達佩斯的考察中更加註意學術上的自我反省。我們站在科學院前面,不僅正好能望見眼前正右方的斜拉索橋,也能看見越過橋的對面小丘上的城市,不用轉過脖子去,我們的左前方就是那座葛蘭夏姆大樓大門,真是一幅美麗的風景畫。此時,一位友人慢吞吞地說起來: “武裝的市民從橋的對面(布達)攻擊駐紮在佩斯蘇軍坦克陣地。” 1956年的巷戰從10月23日開始,到10月30日雖然布達佩斯市民死傷了5萬,但是形勢似乎對匈牙利“有利”,儘管那時並沒有攻下斜拉索橋到馬爾基特橋的佩斯一側的蘇軍陣地。斜拉索橋的橋堍、羅斯福廣場上與葛蘭夏姆大樓比鄰的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總部,所以,蘇軍必須保持它的安全。早先駐紮在匈牙利的一部分蘇軍士兵,看到廣大市民部分老幼男女都紛紛參加戰鬥,發生了動搖,甚至開始保持中立。另一方面,納吉·伊姆雷新政權抱有幻想——以為蘇軍會撤軍,沒有想到這種事態之所以會延續至11月2日,是因為蘇聯方面正在替換和調動部隊。2日蘇聯重新開始全面進攻,投入了20萬人馬、4700輛坦克和800架飛機。這一段時間裡蘇軍與親蘇派武裝守衛的據點的地名卻是羅斯福(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姓命名)廣場。匈牙利市民持槍從布達發起進攻這一據點時,槍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武器了,此外唯一可以憑藉的掩體只有橋上的欄杆。欄杆中有幾個是像座小塔一樣的柱子——一邊4米寬的正方形的柱子,但是,橋不僅長,而且寬度橫列兩輛大型卡車綽綽有餘,所以如果從多瑙河左岸狙擊進攻者的話,橋上沒有進攻者可以隱身之處。不用說,對岸正面等待著的是坦克的砲口。處於戰術上這樣的不利的位子,即使外行也一看就明白。或者說正因為是外行,只要看到這一要素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我一聽到要從這斜拉索橋衝過去,就不假思索地反應:“這怎麼行呢?這不是餵砲彈去送死嗎?為什麼要冒這險?……”* 我不由自主露出責備的口氣,但是無論怎麼說,這只能說是太危險的進攻。當然,當時他們都 被擊倒在橋上、或被擊落到多瑙河中去。與擁有豐富的水量多瑙河相比,他們的鮮血也許是微不足道的量,但是可以說追求自由和正義的人們的鮮血染紅了多瑙河。多瑙河畔的薔薇花也變成了血紅色的薔薇花。我的批判可能完全是無意義。儘管這是成功可能性極小的進攻,可是作為神風特攻隊的本家的日本人沒有批評的資格,何況神風特攻隊及其夢想“回天”,與斜拉索橋上的這次進攻有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即使都是抱著犧牲的信念去進攻,布達佩斯還存在渡過多瑙河獲勝的可能性,生還的可能性也不是說完全沒有,而且,就進攻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來說,兩者也不能相提並論。進攻的話,即使犧牲一點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也不能因此就說這是為了去送命的進攻。從葛蘭夏姆大樓大門邊牆上的彈痕的角度來看,都是布達佩斯市民射出的子彈。誰都會做出與我同樣的反應,因此沒有人反駁我前面那些不假思索的發言。人們不對我做什麼說明,也不表示處憤慨,只是默默地遠眺著橋、城牆和廣場,正因為他們的沉默,促使我不得不深刻地自我反省,甚至要問自己:我一直在思考的作為理解他者的知性的經濟人類學,究竟是什麼?如果歷史是這樣的話,那不是歷史女神對人類的開玩笑嗎?市民們冒死進攻的蘇軍陣地竟然是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姓命名的廣場,而發起進攻市民所處的布達一側的唯一的基地,卻是城的小丘下面的莫斯科廣場。追求“馬扎爾的事物” 我只能邊反省、自律,邊稍微整理一下我逗留在布達佩斯期間及其前後所收集的信息。讓布達佩斯沸騰起來的不僅有波蘭尼兄弟,這個城市還孕育出很多傑出的天才。文學家可以列舉出阿迪·安德烈(Ady Endre, 1877-1919)、盧卡奇、巴拉茲·貝拉(Balázs Béla,1884-1949)、貝拉·福加拉希(Béla Fogarass,1891-1951);音樂家有巴爾托克·貝拉( Bartók Béla,1881-1945)、科達伊·查爾坦(Kodaly Zoltan);還有佛羅倫薩·夏多爾(Ferenczi Sándor,1873-1933)、羅海姆·蓋扎(Róheim Géza,1899-1953)等精神分析心理學家,此外還有如歐根·維格納(Eugen wigner,1902-1995)、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等自然科學家。他們無論是具有猶太血統,還是純馬扎爾人,其之所以優秀,都曾打起“愛國”、“馬扎爾傳統”的旗號。如詩人阿迪、建築家萊希內爾·埃頓(Lechner Odön,1845-1914)倡導的20世紀的新藝術(Art Nouveau)、音樂家巴爾托克、科達伊和多霍納(Dohná Emò, 1877-1960)都直截了當地打出這樣的旗號,佛羅倫薩·夏多爾更是親身參加民族運動。羅海姆·蓋扎雖然沒有與民族運動有什麼大的聯繫,可是他的工作結果完全可以說是屬於馬扎爾的。波蘭尼兄弟中的卡洛伊(卡爾·波蘭尼),他的社會科學理論中最主要的概念是人類社會普遍是一個非市場的社會,這個理論的根底顯示出他是堅持思考共同體集合的道德觀念那種立場。雖然他是出生於維也納的猶太人,但是他的自我選擇——始終認為自己是個馬扎爾人,至少公開承認自己是在馬扎爾文化孕育下成長起來的。弟弟米哈伊(邁克爾)也同樣如此。先是研究生物化學,也關心道德對於人類具有何種影響的問題,進行獨自的研究。他所謂“潛入(indwelling)”方法正是理解其他文化的關鍵。這個概念,是他從1918年和1956年兩次匈牙利革命的經驗中得出(身在國外親歷1918年革命,1956年革命的體驗),強化思考的結果。我所關注的,這個群體,不僅是波蘭尼兄弟,眾多的布達佩斯天才,大多是1880年代出生的同一個時代的群體,幾乎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政治動亂中、與布達佩斯大學為中心的進步學生實踐運動團體或多或少有一定關係,他們決不是單純的思辨型的知識分子,決不是那種無視祖國的現實自我實現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後來都不得不背井離鄉,流亡到奧地利、德國、美國,而當年在布達佩斯時持反奧地利、反奧匈帝國、反柏林、反維也納的立場,這些觀念對於他們的一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據德魯克說,出生於維也納的波拉尼·卡洛伊的德語比馬扎爾語更好。他發起捍衛馬扎爾文化運動,雖然激烈批判波爾什維克主義反民俗的政策,但是,為了保衛馬扎爾傳統卻在1919年5月加入了匈牙利共產黨,我想這不就是為了弘揚至1910年代在馬扎爾國內尚未奮起的千年王國精神嗎?1956年也和1918年、1919年一樣,匈牙利人為了揭起弘揚19世紀的馬扎爾民族主義者的科斯特(Kossth Lajos,1802-1894, ——譯者)的旗幟。1956年市民掌握的電台——自由布達佩斯電台,10月30日以後又改叫名為“自由科斯特電台”。無論是1918-1919年革命,還是1956年革命,科斯特倡導的政策目標都是所謂革命與人民課題中最敏感的東西。卡洛伊並不在乎喊出某種戰略上或戰術上的奇特的口號,只是直截、強烈地希望獲得徹底自由的權利,把權力完全交給無產階級——所謂因為“黨”來代表了無產階級,所以支持黨的行動等於捍衛人民的權力的說法,在他看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有破綻的,是不可信的。無論是1910年代革命,還是1956年最為“革命”得起義都是追求一種共同的精神——科斯特的獨立的民族主義。布達佩斯的深處 投靠權利的人們大多蔑視馬扎爾大眾的潮流。在學術界組織內志在成為大學者的人,無論是從學術思想、還是從學術經歷,都不僅不能理解波拉尼·(卡爾·波蘭尼),還看不起他。但是,波拉尼·米哈伊的經歷卻不能完全無視,而且他涉足領域所取得的業績從生物化學、科學哲學到社會科學,人們或感到困惑,或力圖抹煞這些業績。即使無可否認而得到承認的匈牙利出身的天才,像與美國原子能開發計劃出台有密切關係的、數學、物理學都占鰲頭的羅海姆·蓋扎那樣的人物,雖然沒有辦法否認,但還是值得做出正確評價,在全世界範圍內依然屬於傑出卻沒有名氣的思想家。這些天才的匈牙利思想家,不論大小都對“確立馬扎爾的東西”這個課題有著很深的關係。第一章只是個全書的引子。我們必須從馬扎爾人如何看待馬扎爾、布達佩斯的?他們對這個課題是持怎樣的態度?——這樣的視角來考察20世紀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段時期和1950年代又燃起的布達佩斯的起義。那些思想運動和文化運動並不是今天在布達佩斯產生的,而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時期)到1950年代(第二時期),乃至延續到今天,似有一條很粗的紅線貫穿起來的,以各種各樣形態表現出來。比如前面提到匈牙利風格的新藝術民族特色不僅至今還保留在民間製作的金屬雕塑的手杖等工藝之中,也在後現代的藝術品種反映出來。燃燒的布達佩斯、鮮血染紅的 多瑙河的畔薔薇花——這些事件的某種根源不是能通過孤立的歷史過程、表層國際關係中力量分佈來說明的。我認為這不僅對經濟人類學來說,對整個20世紀的思想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問題。可惜認識到這一點太遲了,現在我的馬扎爾語(匈牙利語)還很拙劣,尚未達到能深入研究水平,只能依賴精通馬扎爾語的友人。從整個日本學術界來看,人們一般都不認同我的觀點,而且匈牙利還在進一步變化,這也是無奈的事情;相反,有幾個人認為我的觀點很極端,倒是說明他們關注我的觀點。本書將要展開的故事,是為了究明布達佩斯精神史的一個嘗試。第二章先考察到底是什麼讓馬扎爾燃燒起來的?還在讓他們燃燒嗎?* 我在其他場合也曾用馬扎爾語說過這句話,但是表達時在細微部分發音都有些錯誤,這次脫口而出,卻說得更加準確。又如,Budapest原來應該讀作“布達佩修特”,但是人們都約定俗成叫它“布達佩斯”,我也跟著說“布達佩斯”了;同樣馬扎爾,原來“扎”應該髮長音的,人們都發短音,我也隨大流發短音了。(匈牙利語中,“s”的發音偏於“修” 所以,栗本慎一郎書中都表記為“シュ”,我顧及中國讀者的習慣,翻譯任命、地名時,都翻譯成:“斯”。 ——譯者)我在其他場合也曾用馬扎爾語說過這句話,但是表達時在細微部分發音都有些錯誤,這次脫口而出,卻說得更加準確。又如,Budapest原來應該讀作“布達佩修特”,但是人們都約定俗成叫它“布達佩斯”,我也跟著說“布達佩斯”了;同樣馬扎爾,原來“扎”應該髮長音的,人們都發短音,我也隨大流發短音了。(匈牙利語中,“s”的發音偏於“修” 所以,栗本慎一郎書中都表記為“シュ”,我顧及中國讀者的習慣,翻譯任命、地名時,都翻譯成:“斯”。 ——譯者)我在其他場合也曾用馬扎爾語說過這句話,但是表達時在細微部分發音都有些錯誤,這次脫口而出,卻說得更加準確。又如,Budapest原來應該讀作“布達佩修特”,但是人們都約定俗成叫它“布達佩斯”,我也跟著說“布達佩斯”了;同樣馬扎爾,原來“扎”應該髮長音的,人們都發短音,我也隨大流發短音了。(匈牙利語中,“s”的發音偏於“修” 所以,栗本慎一郎書中都表記為“シュ”,我顧及中國讀者的習慣,翻譯任命、地名時,都翻譯成:“斯”。 ——譯者)
《布達佩斯的故事》試讀:第二章迎接革命與恐怖暴風雨的來臨——波蘭尼的一家
彼得·德魯克打來的電話 1980年5月底的一天,我趁學術研究會休息的間隙給家裡打個電話。電話中妻子告訴我一個讓我大吃一驚的消息:“有個叫布魯克的人,用拙劣的日語打來電話!” 我對妻子說,不是布魯克,一定是那大名鼎鼎的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教授來電話,與我約見面的時間。聽了我的說明,輪到妻子要跳起來了,問我:你怎麼在東京已經德魯克見過面了呢?她不知道把我與德魯克聯繫起來的是《旁觀者的時代》。1 德魯克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旁觀者的時代》中,有一章敘述以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為首的、天才的波蘭尼家族的業績。那書中,“波蘭尼”被寫作“波拉尼”,其實,從馬扎爾語的原來的發音來說,確實應該拼寫成“波拉尼”,所以稱之為“波拉尼”也不錯。讀到這一章所敘述的關於波蘭尼一家的內容,因為與我已知的大相徑庭,讓我比從妻子那裡聽到他來了電話還要感到吃驚。我知道德魯克來過日本好幾次,所以一直在等候他再來日本時候,想向他請教關於波蘭尼一家的事情,我通過日本的出版社,寫信給德魯克,大概是德魯克讀了我的信後,突然直接打電話來我家。我也沒有想到他會直接打來電話,妻子感到突然和吃驚也在情理之中。維也納時代的波蘭尼與德魯克 後來成為經營學學者的德魯克還未滿18歲在德語的雜誌上發表了為了投考大學寫的論文《巴拿馬運河及其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這雜誌就是《奧地利國民經濟學者》(Der Osterreichsche Volkswirt)。該雜誌的主編註意到這篇文章,因此邀請德魯克參加雜誌的編輯會議。1927年聖誕節上午8點召開的會議。充滿緊張感的德魯克當然很準時地到會。主編和編輯部成員也已經在場,但是會議等了很長時間還沒有開始。德魯克等了四十分鐘,感到很詫異、因為等候時看到的是一位邊哼著“張作霖”、“毛澤東”等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歌詞的怪曲子,邊發出怪叫的奇怪人物——此人就是後來與他長期交往的經濟人類學學者、當時該雜誌負責處理海外信息的副主編卡爾·波蘭尼。會上,身體遠比德魯克魁梧的卡爾·波蘭尼開始與其他編輯論戰。他的觀點是,那時候華爾街的股市呈現的泡沫只是一種資本家趕到繁榮的幻覺,是2、3年以後必然要到來的經濟危機的前奏。發言中,他還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已經死亡,蘇聯的政治不過是一種新的東方式的專制政治之後,接著又津津有味說應該採用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可是他的這些大論都遭到其他編輯們的反對。接著,編輯會議討論下一期的刊載什麼主題的論文,卡爾·波蘭尼警惕經濟危機到來的論題,在5年前已經刊出過,所以被否定了。之後,波蘭尼又提出關於奧地利國內政治鬥爭問題,討論到這一議題時,18歲的青年德魯克發問:“討論希特勒有支配整個德國的可能性,怎樣?”與反對波蘭尼提出的論題相比,德魯克的建議遭到編輯們更為強烈的一致反對。編輯們都認為,希特勒在之前的選舉中已經敗北,猶如已經死亡。可是,波蘭尼贊同德魯克的擔憂,想讓他來寫篇關於這個主題的論文,結果當然遭到全體編輯的反對而未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了30多年的今天,我們再回顧所有的歷史過程的話,德魯克和波蘭尼當時的判斷無疑是正確,其他的編輯缺乏遠見,過分關注眼前短暫的動向得出錯誤的判斷——今天誰都能看得清楚。凱恩斯理論在1929年華爾街股市暴跌之前,在波蘭尼自身的經濟人類學問世之前,已經全球風靡。但是,在以維也納學派的老根據地的維也納的學術圈裡的、這些經濟學刊物編輯等知識分子中,凱恩斯理論都被忽視。今天作為現代經濟學的批判者、連凱恩斯理論也批判的卡爾·波蘭尼,二 戰前提醒同事們要關注凱恩斯理論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結果,希特勒統治了整個德國,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悲劇,卡爾·波蘭尼的妹妹也因為是猶太人遭到屠殺。她在集中營中是如何死去的至今還沒有搞清楚。總之,波蘭尼和德魯克當時具有共同的學術興趣,德魯克對年長的波蘭尼具有那種超群的見解瞠目以對。卡爾·波蘭尼當時41歲,那天因為正好是聖誕節,德魯克還到波蘭尼住的公寓去吃了一頓聖誕“年夜飯” 但是,德魯克後來回憶說:“那天他家裡拿出來的飯局可以這樣用文字來表達:'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難吃的一頓飯'”。而且那天波蘭尼家人,即波蘭尼及他的妻子伊洛娜、小女兒、伊洛娜的母親——一位匈牙利貴族出身的老太太,也不迴避德魯克這個不熟悉的客人在場,討論起下個月的生活費問題來。德魯克無意之中正好看到卡爾的工資支票,令人吃驚的高工資,終於熬不住了插嘴:“也許是我多嘴,剛才看到波蘭尼博士的工資支票,那樣的工資用不著過你們所說那樣節儉地生活呀!” 對這個當然的問題,卡爾美麗的妻子伊洛娜用嚴肅的口氣說: “我們一家有自己的邏輯。現在維也納有很多從匈牙利來的難民——共產主義及其以後的白色恐怖造成的難民。……卡爾的支票上工資全部捐贈給貧困的難民,用別的途徑賺來的錢來維持家用,對於我們重視理念的人來說,這種做法是理所當然的。”2 《大轉換》問世 那就是德魯克與卡爾·波蘭尼交往的開始。波蘭尼流亡在英國時期(1933年至1941年,大戰期間還曾一度回到英國)他們之間的友誼一直發展下去。波蘭尼到了美國,是德魯克的介紹,他獲得了兩年佛蒙特州的一所有名的貝寧頓女子學院的教授職位。1941年德魯克不僅給波蘭尼介紹了貝寧頓學院的工作,還為他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有了這筆研究經費,波蘭尼才寫出了《大轉折》這部名著。總之,波蘭尼在維也納時,能理解這位才十多歲的德魯克;德魯克也已開始就仰慕波蘭尼這位業已41歲的前輩的才能。當德魯克自己也在學界具有很大影響力時,成了促成波蘭尼的經濟人類學的誕生的學術“助產婆”。在英國甘於貧困生活的波蘭尼,如果沒有德魯克的幫助的話,缺少這樣的動力(pathos)鼓勵和場域(tops)存在,這個世界上也就不會誕生波蘭尼派的經濟人類學。關於幫助波蘭尼事情,我曾直接對德魯克表示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也很高興接受了我的謝意。但是,我在維也納進行調查時,發現波蘭尼的妻子伊洛娜談起德魯克,從她自己“角色”的立場出發,表示其獨特的看法。她認為,因為德魯克完全不知道左翼革命運動的實際情形,所以他書中許多敘述是不真實的。比如,波蘭尼家在維也納的住所是福爾加爾廷街203號,卡爾與他的弟弟曾交替住在那裡,可以說是波蘭尼家的一個據點。其所在地區並不是德魯克在《旁觀者的時代》一書中描述的貧民區,即使在今天依然完全可以說是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偏上的公寓住宅區。為了拜訪波蘭尼的舊居,我從著名的聖斯蒂芬教堂以北300米左右的、多瑙河右岸的斯維藤廣場乘電車出發,越過多瑙河,行走2公里半左右下車。途中必須經過一條叫做布拉特爾廣場的馬路,這條馬路很熱鬧,有點像下層市民居住區域那種雜亂的風情。波蘭尼住在那裡的時候,這一帶怎麼樣,就不得而知了,今天那裡還建造了一個兒童樂園。可能以布爾喬亞出身聞名的德魯克眼光看來那是一個貧民區,而且那天正好是聖誕節,街頭人群擁擠。這市內電車行駛穿過布拉特爾廣場後,在左邊不到500米的地方必然可以望見灰濛蒙的室內電車的車庫及其密密麻麻的高架電線。德魯克回憶中說是貧民區,必定是這些因素造成的錯覺。在喧鬧的布拉特爾廣場和高架電線的誘導的記憶中,於是寫下這樣的情景:“棚戶的小屋子和廢車場”。實際上是市內電車的停車場及其高架電線。不管德魯克的記憶受到何種干擾,總之,那一帶即使說不上高級住宅區,至少也可說是中產階級住宅區,所謂住宅區,是指公寓林立,非常閑靜的街區。維也納革命運動卡爾·波蘭尼妹妹索非亞的次女瑪麗婭·塞奇·梅爾茲博士在新藝術館對面的一個維也納的咖啡館裡這麼肯定地對我說:“那一帶是典型的中產階級住宅區!” “是這樣嗎?波蘭尼夫婦收入不菲,很多錢都不用在日常生活上,那是事實嗎?”我問。這位66歲索非亞退休前是經濟學刊物的編輯,告訴我意外的事實。她與前夫開始與卡爾住在同一幢公寓裡。曾與我電話聯繫的那位塞奇先生果然是奧地利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就是索非亞的現在的丈夫。我注意到說到這個話題時,這位女經濟學老學者的兩頰微微泛紅,所以我沒有問她與前夫分手的原因。已經在布達佩斯作了一些調查的我,不難推測那也是因為在納粹統治時代。前夫當然也是猶太人,從事反體制的革命運動,當時革命鬥士的波蘭尼夫婦都支援他們的秘密活動。所謂革命運動,有兩種類型。波蘭尼一家、卡爾的妻子伊洛娜,實際是與下面要詳細談到的布達佩斯民族主義運動這個共同的根底有緊密聯繫的。他們不從屬於昆·貝拉等人的匈牙利共產黨,屬於另一種潮流的左派。伊洛娜不僅因為她是卡爾·波蘭尼的妻子而聞名,作為社會活動家的知名度也超過昆·貝拉及共產黨內的左派領袖們。她雖然是個革命者,可是原則上絕對反對紅色恐怖和布爾什維克的官僚統治,所以流亡到維也納之後,伊洛娜已經不聽命於匈牙利共產黨在維也納的領導,1922年由於與匈共的對立加深,被匈牙利共產黨開除出黨。雖然被開除出黨卻並不退出革命運動,以後仍始終參與匈牙利的解放運動。結婚後,卡爾也支持她的參與的革命運動。伊洛娜在維也納還發起一個以她為中心的左派工人運動。後來,1934年奧地利國內政治衝突激烈時,組織起成武轉的奧地利自衛同盟。關於這一事業的歷史,在卡爾故世後,她用全副精力撰寫了《擁有武器的工人》3在1978年出版,霍布斯鮑姆為該書寫了序言。波蘭尼的收入都用於這些事業,這就是德魯克第一次到他們家時,他們每晚要那樣節儉度過的緣故。53年後,我在夕陽下沿著他們當年的足跡走在布拉特爾廣場大街上,回想著兩次大戰之間那激蕩的年代,卡爾·波蘭尼把那年代稱為“大轉換”的時代,在1920年代維也納那個聚集了一個力圖以知性把普遍人性還原成普遍原理並由此使得社會激烈震蕩的知識群體中,也只有卡爾·波蘭尼一個人發現這個時代正處於“大轉換”之中。因此,當時擔任著名商業雜誌副主編的卡爾·波蘭尼不能把自己金錢的真正的用途告訴剛相識的年輕的德魯克,把自己非常節儉地生活真實原因告訴德魯克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他並不是把金錢來援助普通流亡來的難民,而是資助了當時的革命運動。與德魯克相識7年後,30歲時,也是她顯示最成熟的美的時期,伊洛娜成了奧地利內亂中的左派領袖,在現代史上留下了她的足跡。美麗的婦人門——德魯克的回憶1980年5月在東京,德魯克教授用回憶遙遠往事眼神,反復向我說起伊洛娜是為美女,當場我卻並不在意,聽過算數。那是有兩個原因:其一,我自己也為了把伊洛娜和波蘭尼介紹給日本讀者,曾於伊洛娜有過幾次通信往來,伊洛娜對我在信中表示的那些過分樂觀的想法,多給予嚴厲的批評,鑑於這個前提,說實話,伊洛娜在我頭腦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是個“嚴厲的老太太”,沒有聯想成一個妙齡女郎的餘地;其二,不僅對伊洛娜,波蘭尼家的每個女性,在德魯克敘述時和筆下都描繪成容姿優雅的美女,所以我認為那是因為這位經營學大師對自己長相太缺乏自信、自卑的緣故,我甚至對他的自尋煩惱有點同情。德魯克在與我談話時,還介紹另外兩個波蘭尼家的女性——卡爾的姐姐拉烏拉及其女兒(卡爾的外甥女)愛娃,連連稱讚她倆是美女,對愛娃的評價是:“是我一生碰到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位。” 本來我對德魯克的頭腦和理論非常看重的,贊同他的理論:不僅因為他的理論不是取悅大眾那種庸俗的東西,而且因為他早期的著作,如《經濟人的終結》(1939年)、《產業人的未來》(1934年)中可以看到他指出市場為主體社會的必然會動搖並提出如何對應的問題,也因為他持這樣觀點,所以流亡到英國、美國之後和波蘭尼成友情還保持下去。在《旁觀者的時代》中,他也不隱瞞地談到屢屢與波蘭尼展開論戰往事,那是事實,所以我並不感到驚奇。但是,現在他強調“這個是美女”,“那個是帥哥”,即使不是我,無論誰聽了後都會產生不信感,也會有我前面那種想法——認為德魯克先生對自己長相太缺乏自信。聽者有這種想法也無可厚非。但是,我的想法又是一種難以原諒的失禮的誤解。三個月後,我親自去布達佩斯調查,採訪中雖然沒有聽到人們使用“世界上最美”這樣的讚詞,但是每次聽到的都是“非常美麗”,“很漂亮”的美女等評價、證詞,其中,歷史研究所的利特瓦·傑爾紀博士閉上眼回想起伊洛娜說:“她真得很美!”(Sh )薩鮑·艾爾維圖書館館長萊梅特·拉斯洛博士談起拉烏拉也是連連讚道:“美女,美女!”還有一個人發現我對懷疑德魯克的關於讚詞,拿出照片給我看。利特瓦博士、萊梅特博士都不與伊洛娜、拉烏拉同一世代,也未曾親眼見過她們年輕時代的美貌。總之,布達佩斯的知識分子中,流行著伊洛娜和拉烏拉美女的傳說。從拙著所刊的照片,多少可以理解這樣的傳說。但是,遺憾的是不能把人們傳說她們美麗的那種熱情也完全呈現出來,更遺憾的事情是我也沒有能夠複製自己所看到的她們最美的照片。她們的美必然留在下面介紹的沸騰的布達佩斯精神史中。當然並不僅僅是外貌的美。我在布達佩斯時,當時已經拭去了自己的疑問,可還是留下半點疑惑,雖然這個疑惑與先前的疑問無關:只要這樣的花季美女高叫幾句“打倒腐朽的貴族制度”、“進行反對戰爭的戰爭”之類口號(這是伊洛娜想出來的反戰運動的宣傳口號),人們就接受了?布達佩斯大學就全校罷課了?——豈非太令人羨慕了;何況伊洛娜自身是貴族出身,德魯克在維也納波蘭尼家遇到的伊洛娜的母親海倫,是住在靠近捷克邊境齊尼埃城堡裡真正的馬扎爾貴族家出身,海倫的父親擁有男爵頭銜。這也是德魯克說他吃了一頓一生最難吃的聖誕大菜的原因:貴族出身的貝卡西·海倫根本不會烹調做菜。據瑪麗婭·塞奇·梅爾茲等人介紹,伊羅娜在外從事社會活動,家務全交給母親處理。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卡爾一家是猶太人,聖誕節對他們來說,是普通的日子,沒有當作重要節日。我沒有看到伊洛娜母親海倫她那波蘭貴族出身父親阿爾弗萊特·多欽斯卡照片,對他的長相沒有一個印象,但是根據各方的介紹,可以推測他也長得端正。父親阿爾弗萊特在1900年代中期,拋下才7、8歲女兒伊洛娜和妻子海倫,去美洲新天地追求發展。據親戚們說,大約在1907年在芝加哥附近失踪,與政治無關,單純的殺人事件;也有人說他還活著,到底結果怎樣,沒有確實的答案。人們對我的刨根究底的詢問,不能只作有根據的回答。沒有得到任何遺言失去父親的伊洛娜在馬扎爾貴族外公貝卡西(Békassy)家長大,姓照舊用父親的波蘭的“多欽斯卡”姓。假如按照匈牙利的念法,姓在前,名在後,也是用“多欽斯卡”這個波蘭姓。所謂“多瑙河畔的薔薇花”,既是指布達佩斯的薔薇花,也用來謳歌美女革命家多欽斯卡·伊洛娜,而“伊洛娜”這個名字卻完全是出自馬扎爾語,相當於其他歐洲語言中的“海倫”,奇怪的是馬扎爾人的母親卻用海倫(Helén)作名字。這是對德魯克所謂波蘭尼家難吃的聖誕夜餐另一種解釋,即使她們只端出一碗煮土豆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布達佩斯精神史的序幕前面已經談到考察1910、1920年代匈牙利精神史時,與思想家卡爾·波蘭尼相比,其實,革命家多欽斯卡·伊洛娜與揭開這精神史序幕有更密切的關係。德魯克在《旁觀者的時代》一書中最富有衝擊力的一章《波蘭尼一家》的開頭敘述了多欽斯卡·伊洛娜的一生的軌跡,很遺憾,其中有許多要糾正的謬誤,如他誤把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南斯拉夫的鐵託也作為受波蘭尼一家思想影響的副產品,所以有必要邊糾正德魯克的誤記,邊揭開20世紀初布達佩斯精神史的序幕。至今人們尚未充分認識到產生許多天才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在20世紀初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把這些當時的大師的名字一一列舉出來:波拉尼·卡洛伊(卡爾·波蘭尼)、波拉尼·米哈伊(邁克爾·波蘭尼)、音樂家巴爾托克·貝拉、建築家萊希內爾·埃頓、心理學家佛羅倫薩·夏多爾和理學家馮·諾伊曼。這些大師業績都在追求馬扎爾民俗文化積累起來的,都與馬扎爾民俗文化運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個群體另外一個特點是,這些追求馬扎爾民俗文化的大師大多是猶太人,卻與排斥周邊少數民族的沙文主義不沾邊。這一特點也表明布達佩斯20世紀初的思想領域的歷史,並不亞於1920年代維也納精神史的輝煌。而且,這段精神史的特點,這並不是消極意義上僅僅局限於某一方面,其知性形態及其深度、廣度最後都被收斂在波蘭尼兄弟思想之中,這也是我想探索的課題。要說德魯克書中記敘的錯誤,那書中言及的人、城市的印象幾乎都有錯,下面我們只要追踪伊洛娜——不到10歲就失去父親卻一直沿用父親的姓氏,戰鬥一生的人生軌跡就可以知道她與拉烏拉的美,決不只是局限於物理的、外貌的形態美。此外,我們追尋波蘭尼的家史後,還可以搞清楚布達佩斯地波蘭尼一家與墨索里尼、鐵托、新生巴西運動、基布特社會主義運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到底有沒有關係。多瑙河薔薇花——妖精多欽斯卡·伊洛娜 前面已經提到伊洛娜在離開與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很 近的外公的城堡里長大的。那麼,讓我們先來看看德魯克是怎樣記敘的。根據他的說法,伊洛娜的父親是匈牙利國家鐵路總裁,他的前任是伊洛娜丈夫卡爾·波蘭尼的父親。卡爾·波蘭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從軍,負了重傷,在醫院與護士伊洛娜邂逅後,戀愛、結婚,這發生在布達佩斯。但是伊洛娜只有17歲,已經是共產黨領袖。4 這回憶是德魯克無限羅曼蒂克的遐想,充滿了難以想像的錯誤。首先。伊洛娜的父親阿爾弗萊特是波蘭貴族出身,屬於下級貴族,出自一個完全敗落的家庭,在維也納只是國家鐵路公司的一個普通職員,不曾擔任國鐵總裁。所以,國家鐵道總裁的女兒伊洛娜在醫院裡作為護士與傷兵邂逅的浪漫故事更加離奇。前面已經提到了,實際是阿爾弗萊特為了追求世俗社會的成功,下決心留下妻與子,悲壯地遠渡北美。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芝加哥附近遭暗殺遇害,可以說是不幸的一生。還有,共產黨是1918年由昆·貝拉帶著秘密使命從蘇俄回到匈牙利之後,才在匈牙利國內組織起來的。伊洛娜並不是地下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而是布達佩斯大學革新派學生團體伽里略同盟中心人物。雖然她以後成為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但是17歲的時候,無論是公開的共產黨組織,還是地下共產黨都尚未誕生,最根本的問題,卡爾·波蘭尼與伊洛娜相識並不是在布達佩斯。根據伊洛娜自己執筆的、為卡爾·波蘭尼遺著《人類的經濟》寫的序言5,他們是1920年在維也納郊外相識;誤傳的所謂她曾積極參與領導的伽里略同盟,實際是卡爾·波蘭尼發起組織的,擔任第一任組長的一個小群體: “當時我也不知道伽里略同盟中曾有卡爾·波蘭尼,不僅該同盟成立時,我只有10歲,而且我從事的社會活動與卡爾有時代的差別。在我參加的社會活動年齡的年代,凡是與革命活動沒有關係的事項都不納入討論的範圍。也不利用任何東西。我從1917年開始,以後19年間所屬的一個社會活動的小群體與伽里略同盟那個群體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任何共同的基盤。”6 確實如此,在布達佩斯生活年代,她根本與卡爾·波蘭尼無涉。她不是猶太人,如前所說是貴族出生,與其他的社會活動家不同的 是,她本人與布達佩斯大學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她完全是作為職業革命的領導人接近大學學生團體的。伊洛娜上的大學是與愛因斯坦同一所大學——瑞士的蘇黎世工科大學,在那裡學數學和物理學,參加在瑞士伯爾尼齊美爾沃爾德第二共產國際,帶著這個它的使命來到布達佩斯。她在布達佩斯感到憂慮的是:1913年以來奧匈帝國取分離統治政策匈牙利帝國內不僅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處於被壓迫民族地位,馬扎爾人的壓倒多數都是農民,在保守的政治家戴薩·伊斯特瓦恩(István Tisza)的統治下,匈牙利在精神上處於閉塞的停滯狀態。之所以說戴薩採用親奧地利政策,因為他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權威來壓制其他民族。他自身對奧地利半炫耀、半恫嚇的殺手鐧是奧地利所依賴的匈牙利供應的糧食。他採取的政策代表著當時馬扎爾人的統治階層的無能的排外主義。第一次大戰爆發,匈牙利當然站在奧匈同盟關係的立場上參戰,但是匈牙利控制的國內的塞爾維亞人都站在協約國一邊,羅馬尼亞在1916年8月倒向協約國陣營。1917年7月以後,塞爾維亞人的目標要建立一個不僅將奧匈帝國內的塞爾維亞人還要把現在南斯拉夫北部克羅地亞人、捷克南部的斯洛伐克人在內的南斯拉夫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戰況對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有利,但是到了1917年,各方面的形勢對匈牙利不利起來。於是匈牙利帝國內部各民族自然趁這時機結成反馬扎爾聯盟。戴薩也因此越來越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奧地利也越來越難以操縱戴薩,因為奧地利本國糧食不足,不得不依賴從匈牙利進口,完全無法駕馭戴薩,所以無法“干涉”匈牙利的內務。1916年11月登位的奧地利新皇帝卡爾,計劃瓦解部分馬扎爾貴族專制體制,在匈牙利導入普選權制度。匈牙利首相戴薩以停止提供糧食進行威脅,卡爾只能作罷。戴薩成了成功維持匈牙利貴族制度的象徵性人物。戴薩為首的執政黨是1910年創立的號稱國民工人黨的保守的布爾喬亞政黨,它合併了1875年至1905年長期執政自由黨。戴薩自己兼任匈牙利工商銀行行長,也是個擁有大批土地的貴族。盧卡奇的父親是民間信用銀行的總裁,是戴薩主要的政治上的支持者。伊洛娜回到匈牙利的1917年,匈牙利原先蘊藏著各種矛盾衝突一下子噴發出來。1916年製造彈藥武器軍工廠工人自發罷工,在社會各種勢力新的激烈衝突中,大地主貴族卡洛伊·米哈伊組織了“卡洛伊黨”,號召國民和解、團結;卡爾·波蘭尼的年長的好友亞西·奧斯卡組織了激進市民黨(也稱布爾喬亞激進黨)其目標是促成國民團結和民主主義革命。當時,曾在布達佩斯大學執教(無編制講師,猶太人不能當教授)、以後流亡到美國俄亥俄 州奧巴林大學政治學教授、留下好幾冊著作7的亞西·奧斯卡,當初與卡爾·波蘭尼在布達佩斯大學都是伽里略同盟的同志。因為伽里略同盟是一個異常寬鬆的組織,談不上在組織裡擔任什麼、什麼職位,那時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然而,1917年卡爾·波蘭尼確實擔任了激進市民黨總書記。從無論哪個方面都不肯妥協的意義上來看,伊洛娜是徹底的激進革命左派,相對來說,波蘭尼追求的是民主革命,是“市民革命”,比較溫和。伊洛娜作為組織者把亞西、波蘭尼創立的伽里略同盟發展成一個革命的學生組織。認識之前卡爾和伊洛娜應該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因為布達佩斯不是一個很大的都市,把伊洛娜推到更高的領袖人物位置的是薩鮑·艾爾維——他是卡爾的表弟。到了1917年年中,伊洛娜已經超越第二國際左派的活動範圍,在布達佩斯獨特的思潮中有了自己位置。她接受薩鮑·艾爾維的命令,要求在不久的5月的某天,派伊洛娜去暗殺黑暗貴族文化體制的代表者戴薩,本來伊洛娜年輕豐腴身上要藏把左輪手槍,豁出去走上街頭,淹沒在人群之中屏著氣、緊張地等待同志傳來開槍的信號的。幸虧組織上得到消息:奧地利皇帝卡爾的壓力下,戴薩已經決定辭去首相職務,取消了這次暗殺。真的,否則差一點貴族小姐伊洛娜要作為恐怖分子登上歷史舞台了。命運發生了180度轉變,是年,她不是作為恐怖分子,而是作為反戰的和平主義運動領袖被判處徒刑的,那年才20歲。1918年10月爆發“菊花革命”,11月她釋放出獄,幾乎被關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她去監獄探望那些在緊迫的革命運動由於恐怖活動中負傷、被捕的同志。為組織者把亞西、波蘭尼創立的伽里略同盟發展成一個革命的學生組織。認識之前卡爾和伊洛娜應該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因為布達佩斯不是一個很大的都市,把伊洛娜推到更高的領袖人物位置的是薩鮑·艾爾維——他是卡爾的表弟。到了1917年年中,伊洛娜已經超越第二國際左派的活動範圍,在布達佩斯獨特的思潮中有了自己位置。她接受薩鮑·艾爾維的命令,要求在不久的5月的某天,派伊洛娜去暗殺黑暗貴族文化體制的代表者戴薩,本來伊洛娜年輕豐腴身上要藏把左輪手槍,豁出去走上街頭,淹沒在人群之中屏著氣、緊張地等待同志傳來開槍的信號的。幸虧組織上得到消息:奧地利皇帝卡爾的壓力下,戴薩已經決定辭去首相職務,取消了這次暗殺。真的,否則差一點貴族小姐伊洛娜要作為恐怖分子登上歷史舞台了。命運發生了180度轉變,是年,她不是作為恐怖分子,而是作為反戰的和平主義運動領袖被判處徒刑的,那年才20歲。1918年10月爆發“菊花革命”,11月她釋放出獄,幾乎被關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她去監獄探望那些在緊迫的革命運動由於恐怖活動中負傷、被捕的同志。為組織者把亞西、波蘭尼創立的伽里略同盟發展成一個革命的學生組織。認識之前卡爾和伊洛娜應該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因為布達佩斯不是一個很大的都市,把伊洛娜推到更高的領袖人物位置的是薩鮑·艾爾維——他是卡爾的表弟。到了1917年年中,伊洛娜已經超越第二國際左派的活動範圍,在布達佩斯獨特的思潮中有了自己位置。她接受薩鮑·艾爾維的命令,要求在不久的5月的某天,派伊洛娜去暗殺黑暗貴族文化體制的代表者戴薩,本來伊洛娜年輕豐腴身上要藏把左輪手槍,豁出去走上街頭,淹沒在人群之中屏著氣、緊張地等待同志傳來開槍的信號的。幸虧組織上得到消息:奧地利皇帝卡爾的壓力下,戴薩已經決定辭去首相職務,取消了這次暗殺。真的,否則差一點貴族小姐伊洛娜要作為恐怖分子登上歷史舞台了。命運發生了180度轉變,是年,她不是作為恐怖分子,而是作為反戰的和平主義運動領袖被判處徒刑的,那年才20歲。1918年10月爆發“菊花革命”,11月她釋放出獄,幾乎被關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她去監獄探望那些在緊迫的革命運動由於恐怖活動中負傷、被捕的同志。放出獄,幾乎被關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她去監獄探望那些在緊迫的革命運動由於恐怖活動中負傷、被捕的同志。放出獄,幾乎被關了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她去監獄探望那些在緊迫的革命運動由於恐怖活動中負傷、被捕的同志。